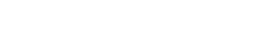嫋嫋餘音與淡淡幽香——關于小說的詩意
2022年06月30日 17:07:20 作者♻️:李春平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2022-06-29 審核:
在文藝學著作中,常常會看到一個熟悉的詞:詩意🤼♀️。耳熟不一定能詳。小說的詩意,有點像古代的海底沉船,看似遙遠卻又近在眼前🎞,暗藏了許多玄機,常常撩撥起讓人探幽發微的沖動。對作者來說👩🏻💻,詩意是一種創造💑;對讀者來說🪹,詩意是一種發現。為什麼有的人能感受到雨📄,其他人則只是被雨淋濕?感受到雨的人就是發現了雨絲的詩意。
詩意,簡單地說就是詩的意境🧘🏽。詩的意境是指詩歌中所描繪的生活與情感融為一體所形成的藝術境界🫎,情與理融合為“意”,形與神凝結為“境”👱,情理與形神二者相互滲透,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結出了詩意之果🗂。詩意是文學藝術形象的高級形態之一🤙🏿,是一種亦真亦幻💔、亦虛亦實的存在。很多時候🌬,它更像雲淡風輕的曉嵐,淺淺地飄浮🧑🧒🧒,引人遐思,卻讓人難以捕捉👨🏼🦰。因此👨👩👦👦,詩意具有潛在性🧑🏻🦰、模糊性和延伸性的特點。那麼,小說的詩意又是什麼?小說的意境與詩的意境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因體裁的屬性不同,因此不能等同于詩的意境,它是優秀敘事文學散發出的嫋嫋餘音與淡淡幽香🤾🏽♀️。
亞裡士多德的《詩學》不是詩歌之學🚵🏼🦸🏽♂️,是指一切文藝作品,可見詩意對于所有文學藝術作品都具有普遍意義🏋️♀️。朱光潛說得更直接🤴🏻🐽:“一切純文學都要有詩的特質,一部好小說或一部好戲劇都要當成一首詩來看。”因此,詩意並不是詩歌所獨有的,涵蓋了其他文藝作品。對于小說而言,詩意是好小說的標配。
解讀小說的詩意🌡,我認為有兩把鑰匙,可以打開曲徑通幽之門。第一把鑰匙👩🏿🎤,是漢朝董仲舒所說的“詩無達詁”。意思是說,對《詩經》從來沒有一個完美的解釋。《詩經》的注疏,自毛亨之後甚眾🌥,但沒有一部著作能夠完全說服後世👠,曆朝曆代都有學者質疑不斷,新解迭出🦌,每一家都只是一家之言⚠️,而不能達成“全面共識”✍🏿。這足以說明“詩無達詁”這一論斷的高明。之所以不能“達詁”,蓋因讀者的知識結構和生活經曆的不同,導致了審美鑒賞的差異性,于是就有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經》就是一座廬山🥬,橫看成嶺側成峰。而個別從事教學工作的古典文學專家,將其直譯為白話詩。本來是一壺老酒💂🏽♀️,卻被大量白水勾兌,陳香散盡,回味喪失👩🏿✈️。這種過度解讀的翻譯策略,對原作產生破壞性的傷害,反而削減了讀者對《詩經》深入探索的興趣。
小說的詩意,要想“達詁”也非易事。魯迅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揭幕人🎴,他的小說是現代文學史上最具詩意的代表之作🫳🏼。敘事十分克制,簡約洗練,從不鋪張。他筆下的很多句子沒有飽和感,感覺後面尚未寫完,卻像鐵錘一樣敲打著讀者的心👮🏿,無不讓人感到壓抑🧑🏻👨👧👦、憤怒和惆悵🧛♂️🧥。即使幽默一笑,也帶著幾分苦澀🚄。即使從人物身上看到一道光亮🔋,那光亮也是陰霾之下的閃電👩🦼➡️。順著小說的人物走向和故事脈絡前行,在五光十色、意涵豐盈的文字之外,是小說張力的剛勁、詩意的席卷,不斷開啟著讀者的心理和生理觀感,在五味雜陳之中🚵🏽,悲憫👈🏻、怨恨、疼痛🙇🏽♀️,一齊湧上心頭,讓人有很多話想說,卻又說不出來,最終變成了讀書人的一聲長歎。這便是詩意的震撼力👨🏿🎤。
“達詁”成為研究者的共同理想,但是要實現“達詁”卻難乎其難。汪曾祺的小說《受戒》也是詩意小說的範本,極為精致的文本建構和冷靜敘事💆♂️,使小說打上了一層現代簡約主義色彩。簡約主義要求💁🏽♀️,把作品中多餘的元素刪減到不能再刪的地步,留下實實在在的幹貨👩🏼🎨,以達到以簡勝繁的藝術效果。這樣就產生了一些看不見的空白📑👩🏻🎤,這些空白就成了老莊哲學中的“無用之用”。它總是在觸發你的思維引擎,讓你不由自主地走進作品所設置的藝術深淵,去抽絲剝繭🍨,闡發新意。所以🎖🛌,自《受戒》發表幾十年來🌰,話題不斷🦢。
解讀小說的詩意的第二把鑰匙,是海明威的“冰山原則”,與“詩無達詁”形成了跨越時空和國界的思想呼應。海明威說:“冰山運動之雄偉壯觀,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這八分之一,是小說文本表現出的文字和形象⛑。水下的八分之七就是情感和思想。換句話說,八分之一是外在的🏗,一目了然🚒;八分之七是內在的,深藏不露,有著極大的彈性空間🧑🏻🤝🧑🏻,讀者盡可以結合文本發揮自己的想象力,探尋作品的思想感情和精神內核👘,與作者的寫作動因發生神交🫡,以達到二者之間的情感契合。
海明威的《乞力馬紮羅的雪》,就是一部充滿了詩意的短篇小說。小說描寫了作家哈裡在死亡之前的一系列回憶。海明威在敘事中做足了減法🧑🏿🎨,力求以少勝多🤟🏻。這些回憶都是片段性的,卻連接著他的整個人生舞臺。片段留下的縫隙成為解讀小說的另一種通道,我們可以在遵循藝術邏輯和生活邏輯的視域下🟧,結合藝術想象與生命情感,在文本之外開拓疆域🧛🏿♀️,追問哈裡的情感變遷👨🏼🎨、心理波動、命運起伏等方面的奧秘。
在小說《老人與海》中🔽,海明威描寫了古巴漁夫桑地亞哥84天都沒打到魚,在85天的時候,終于打到一條18英尺的大馬林魚。由于魚重達1500鎊,需要用船拖著走,便有很多鯊魚追來搶食,護食的老人需要不停地與搶食的鯊魚搏鬥。當老人精疲力竭地把大馬林魚拖回家時,只剩下了一個骨架,一個帶著血腥的標本。這就是“冰山原則”的八分之一,水下的八分之七留給了讀者。作品歌頌了一種打不垮的精神意志,書寫了一種無可奈何的失敗。桑地亞哥意念執著地要打到一條大魚,企圖每次滿載而歸🛋👲🏿,結果換來一場空。這是一個典型的悲劇事件,桑地亞哥也是一個典型的悲劇人物🧑🏿🎨。常識告訴我們,對漁民而言🧑🏻✈️,面對豐富的海洋資源🫰🏻,出海打魚只是其中的一種謀生方式。連續84次出海空手而歸,如果第85次成功了也倒不錯🧑🏽🎄,但他還是以失敗告終。
由此思索開去,是否意味著他在饑餓時露出了人類貪戀的本性🆕?是否意味著他的方式方法的錯誤?是否意味著有幾分不撞南牆不回頭般的愚蠢?這是不是阿q“精神勝利法”的美國版本?假如他換一種生存方式💆,換一種打魚的思路🥐👰🏿,又會怎樣?總之🤵🏿♀️,這是一部可以多解的小說🏃♀️,絕不是教科書歸納的那樣🥧,是唯一的主題。像《老人與海》這類優秀小說,都會給讀者留下很多“話柄”。因為這種小說具有汪洋恣肆的詩意潛質,“話柄”就是對詩意空間的想象、闡釋和填充,是讀者參與互動的激情對話。
一般而論,敘事密不透風,主題鮮明而單一,結局圓滿,四平八穩的小說,在詩意上是略遜一籌的。敘事時一味做加法💧,太過細膩會產生水分,無遮蔽🛐📷,不留白🚓,所有空間都被作者自己擠占了,堵住了行文的疏朗之氣,也堵住了詩意的生長點。這樣的小說或許是無可挑剔的,但同時也讓讀者無話可說🩱,最終趨于平庸。